
第二十四讲:哲人与政治的纠缠——关于柏拉图《第七封信》(下)
法律与文学第二十四讲_下
柏拉图最后又去思考。我们知道柏拉图后期有一个转向,他前期主张“哲学王”的统治,但是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真正的“哲学王”,怎么办?柏拉图最后一本著作叫《法律篇》,他转向了法制。他说,“让西西里和任何地方、任何城邦不要再屈服于任何一个世俗的统治者,而要屈服于法律”。这相当于他失败以后得出来的惨痛的结论,人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法律。
但是很多人还是认为柏拉图是失败的,因为后面小狄奥尼修斯也被推翻以后几年,整个西西里被一个叫提摩勒昂(Timoleon)的人统治,而这个人在八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政治秩序。英国著名的希腊史研究家格罗特说,“事实证明柏拉图主义者即政治理想主义者,花四十年搞不定的事,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以花八年搞得非常好。这似乎又证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无论是从道理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赤裸裸的失败。而且从文献来看,杀死狄昂的两个人非常可能就是来自柏拉图的学生,是狄昂在雅典结交的朋友。我们的结论是可能责人参与政治,是不是对哲学,对政治,对友谊,对友情都是伤害。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现在要总结,柏拉图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去从事政治?其实核心还是为了哲学,柏拉图从事政治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哲学。
我们今天由于波普尔的传统而形成了误读,这个误读就认为,希腊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是我们的同代人。在二十世纪还有很多的名字,当代的叙拉古也不止一座,比如说苏联、纳粹德国等等。而像柏拉图那样的扬帆往叙拉古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比如重庆唱红打黑最风光的时候,中国多少的哲学家知识分子跑到重庆去了。有个人叫马克·里拉,他就给这些当代的“柏拉图”,即所有这些像苍蝇一样依附于权力的哲学家,给他们起到一个名字叫“热爱僭主的知识分子” (philotyrannical intellectuals),其实这是对柏拉图是有误读的。
马克·里拉
我们看柏拉图跟政治的关系,并不是有所求。柏拉图已经没有什么可求的,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向统治者到底求什么?很难说。柏拉图他对自己要有交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哲学的力量到底在哪里?他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空谈家,永远不可能有行动。他顾虑的是哲学是不是仅仅是一番道理,而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哲学是不是只是悬在空中不能落到实处的东西,不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真正的力量。这个传统影响到包括马克思,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真正的哲学不仅是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造世界”。其实都是这样的愿望和翻版。
哲学最早也是一种逻各斯。在柏拉图之前,在希腊有两个史学的传统,一个是希罗多德,一个是修昔底德,他们分别写了古希腊两部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一部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一部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这两部历史著作体现了两种核心观念的冲突,就是言辞和事迹的对立。我更愿意把事迹翻译成“事功”,就是你的言说、讲道理和你的事功之间的对立。我们经常说“立德、立功、立言”,实际上就是“立功”和“立言”之间的对立。在希罗多德那里,当然最重要的是人留下的事迹,光荣的事迹,一种事功。希罗多德把自己与荷马相比,他想要创造一个不朽的声名。而人的行为是比所有的神庙金字塔更不朽,更重要的事迹。我们假期读过荷马史诗就知道,荷马史诗里的英雄的人物,为他们修的纪念碑和城堡可能都已经毁坏了,但他们的英名是万古长存的。什么叫做事迹?事迹是伟大的、神奇的、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能够被记忆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世人所能做的事,他是能够给公众展示的,让所有人看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记载希波战争的,是永远展示希腊人德性的历史的事迹,这个事迹是能够融入历史传统的人的伟大的行为,历史是大写的英雄。
我整个古希腊的历史就是三场战争,一个是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一个是希波战争,一个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三场战争塑造了伟大的文明。希波战争强调的就是事功,但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就不一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强调了逻各斯和言辞的重要性,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里面也有“事功”,但这个“事功”作为伟大的事迹和光荣已经堕落成纯粹的力量和强权的较量。修昔底德非常强调逻各斯和言说或者道理的重要性,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很悲催的主题,他描写当时雅典这个头号的帝国,尽管是城邦,霸权国家,怎么从最高峰一步一步地、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对希腊世界的教师和领导者的地位。战争背后,发现大家都不听道理,逻各斯不如比谁的拳头更硬。雅典的悲剧是,希腊精神当中讲道理的力量被外在的暴力的力量打败了。我们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知道,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演讲—伯里克里的演讲。比如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些话都是著名的演讲里面来的,伯利克里的演讲是最辉煌的篇章。
修昔底德
当时,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繁荣还没有转入失败,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前的演讲表明,雅典的生活方式是全希腊的典范,雅典是希腊民主的学校。雅典人爱美但不奢华,爱智慧但不软弱,使用财富但更多用在实处。他说,我们从事政治的人照看城邦,同时也关心私人生活。所有其他人当他们关注私人的生活的时候,也从来不会忘记要参与政治。所有的公民都参与对于德性的塑造。我们从来不会将逻各斯、讲道理作为行动的绊脚石,而是看做明智行动的准备,这是雅典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从伯里克利的演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雅典人那种高度的自信,那是从内而外发自肺腑的自信,对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民主的那种自豪。
伯利克里
但历史往往是充满偶然的。我们知道逻各斯很快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伯里克利演讲之后的第二年,雅典就发生了瘟疫,而且伯里克利就是在这场瘟疫当中就被夺去了性命。很多人今天假设,假如伯里克利没有被这场瘟疫而夺去生命,雅典说不定不会失败,但这是假设,历史不容假设。这张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年,伯里克利作为最伟大的头号将军在第二年就去世了。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一种偶然的力量,其实偶然本身也是对抗逻各斯的,这是逻各斯被解构、被化解的第一个事件,有外在的偶然。
还有第二个事件,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场著名的辩论,这不是演讲,叫密提林(Mytilene)辩论,这个辩论也是重要的篇章。这个辩论讲的是,雅典有一个重要的城邦、属国叫密提林,他们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背叛了雅典,投奔了斯巴达,但最后密提林又被雅典人打败了,打败以后雅典人就要召集大会讨论如何处置密提林人。第一天他们进行了民主的投票,当时雅典人都是群情激奋,一定要惩罚这些背信弃义的盟友,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决议,就是密提林的所有的男人都要被处死,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要被卖为奴隶。决议作出以后,雅典的民主派就派使者到前线去通知将军们执行这个决议。但是第二天雅典人又后悔了,赶紧又重新召开另一场会议,赶紧派使者把之前的使者追回来。当时民主政治心软的这么一面就体现出来。当时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叫克里昂(Cleon)就说,雅典的后悔暴露出雅典政治的弱点,即过多的逻各斯会破坏政治行动,逻各斯越来越成为行动不再有力、不再明智的一个部分。
我们讲过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也是因为逻各斯太多行动太少。当然我讲哈姆雷特我是解构了这种说法,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哈姆雷特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它是有行动力的,它的悲剧是虚无主义的悲剧,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般的理解是哈姆雷特想该不该报仇,他想的太多。雅典战争时期,他们想的太多了,所以他们行动就犹豫了,行动犹豫可能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言辞和行动的矛盾不仅是延续到普鲁塔克时代,其实也延续到今天。普鲁塔克有一部重要的作品《亚历山大的命运与德性》,普鲁塔克在其中说了一句话,他说,谁是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把整个希腊哲学带到了全世界。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值得玩味的。因为柏拉图有一个最重要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五十多岁的时候成为当时只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的“帝师”。柏拉图三次到叙拉古,想做“帝师”失败了,失意而归。但是亚里士多德教出了最伟大的皇帝。当普鲁塔克说“谁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亚历山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太有意思了。其实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柏拉图好像失败了,哲学失败了吗?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成功地当“帝师”就是成功了,是不是也证明哲学成功了?
普鲁塔克
其实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背后的哲学的观照是一样的,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如何把逻各斯和事功打通,如何把沉思的理论的思考和行动真正地打通。哲学是需要有力量的,是要影响社会的。当然我们说哲学叫做无用之大用,它影响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一个哲学家没有这样的想法。你看所有伟大的哲学家最后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成为力量,如果你不打通这两者,就是柏拉图前面说的“让哲学蒙羞”,就是背叛了哲学,他的关注是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关注。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个口号叫“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培根等人启蒙时代说出来的,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知识,但“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从柏拉图那里面来的。哲学就是知识,哲学要体现自己的力量。但是到了福柯时代,福柯把“知识就是力量”说成“知识就是权力”。换言之,我们还可以倒过来说,权力就是知识。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知识,同样谁掌握了知识谁掌握权力。哲学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其实都是力量,但是它们毕竟是不同的力量。它们怎么结合在一起?它们并不是必然在一起,否则苏格拉底不会死了,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但是也不能说,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力量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有成功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洋洋自得的经济工作者,都以为自己是创造发明,看不起经济学家,但他们不知道所用的这些方法不过是多少年前某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的遗迹而已。换言之,真正的精神总会是产生影响的,他死了,他也会在坟墓里面统治着活人,这是精神的力量。
凯恩斯
哲学和政治怎么去结合?当然我们是要去思考的。这种结合其实在柏拉图看来是靠一种偶然结合在一起的。能不能真正实现哲学和政治的结合,是依靠偶然的因素,而偶然怎么去实现?主要是靠教育。但是我告诉大家,教育是最偶然的东西,因为教育是最复杂的东西,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以为你教育他成功了,你只有教育,他不可能去重演。而且是不是成功,也很难去评判,因为教育没办法比较。
我们知道《理想国》被认为是关于教育学的第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如何培养政治家,培养公民,包括该读什么书,什么书不该读的,其实柏拉图一直在做这个实验。但是当他想真正地去教育狄奥尼修斯二世这样人的时候,没有想到狄奥尼修斯已经认为自己懂哲学了。柏拉图第三次到叙拉古,听说狄奥尼修斯还会写书了,他不需要教育了。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说政治家不懂哲学,而是政治家懂得“半吊子”哲学,这个是最糟糕。他似懂非懂,这个带来的错误是最大的,他还听不进别人的话,我比你懂。他还看不起他的老师,其实他是看到他老师很浅的地方。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就发现往往是那些“半吊子”的学生,你给他讲几句,他就觉得我都懂了,这本书我就不用读了都懂了,我要看复杂的。其实他并没有真正懂,但他以为他懂了。对于这种学生,老师是最无语的,无话可说,只能苦笑一声。其实他没懂,但他以为他懂。其实狄奥尼修斯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承认狄奥尼修斯二世具有哲学家的天赋。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把整个城邦的人民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金质的,一个是银质的,一个是破铜烂铁。人与人之间是有等级的,有差别的。我们害怕一种情况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是说,你本身是破铜烂铁,你还以为你是黄金制作的,你还以为你是“哲人王”,这个很糟糕。但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黄金的天赋也很糟糕。为什么?黄金的天赋他可能从事哲学,但是拥有最好天性的人一旦堕落,更可怕。狄奥尼修斯可能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强调是个偶然的,就是说最好的天性从事哲学,从事政治,能够完成政治和哲学的结合。但是拥有最好天性的人也容易堕落成最糟糕的人。其实这已经不是哲学的问题,这是本性的问题,这是教育的偶然的问题。比如说狄奥尼修斯,他有最好的天性,他太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周围恰恰有很多人劝告他,你不要过哲学的生活,而要过政治的生活。所以说越是最好的哲学天性,越会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统治欲望,而且他认为哲学没什么了不起,仅仅是我的工具而已吗,这就糟糕。
我们衡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你可以发现真正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绝对不是这种“半吊子”,他绝对是最谦卑的,最战战兢兢的。我办公室里面有两句话,从《道德经》里面引的,“圣人犹难之”,“果而不得已”。我最喜欢的政治家是华盛顿,这两句话是最能形容华盛顿。我们知道华盛顿他从来不认为是伟大的军事家,华盛顿的军事成绩一败涂地,他基本就没打过胜仗。他怎么跟拿破仑跟亚历山大比。从政治方面来说,华盛顿也没有太多的政治天赋,他没有太多的知识。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的明星,全是高学历,全是不学富五车、博览群书的人。富兰克林,又是政治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这样的人,华盛顿从哪方面跟他们比都比不上?但是华盛顿是最有威望的。华盛顿是一个测绘员,土地测量员,他把美洲大地全部走遍了,而且华盛顿从来不眷恋权力,三进三退。独立战争被迫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独立战争一胜利把枪杆子一甩,我要回家去当农民去了,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在家里一待待了四年几年。到1787年又不得不出山,因为当时美洲不行,不成立一个国家受不了,华盛顿又被迫出来,他还找借口,我这个又风湿病犯了,我的侄儿又死了,我不想出来。出来以后,参加大陆会议,制定了宪法。他只是当名义的主席,在大陆会议上他不说一句话。日后他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统,当时美国宪法没有总统任期,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再也不干,又回去了。华盛顿就是这种人。“圣人犹难之”,每次战争,他一会埋怨大陆会议没有钱,他的士兵被冻死了,没有衣服穿了,使劲地抱怨,我干脆回去让我担任苦差事干什么。华盛顿每次都是在树林里面去祷告,说我不要干了,叫做“圣人犹难之”,战战兢兢,太艰难了,怎么让我干这么难的事情。
然后叫“果而不得已”。我们知道老子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取得了战争的成果,我“果而勿矜”, “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战争毕竟是残酷的,我们打仗哪怕取得胜利,我们是不得已的,这也是华盛顿的心态。战胜英国也没什么好光荣的,我们是没办法。英国人不走,我们没办法生存不下去,税太高了。他是这么一个心态。
华盛顿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按照柏拉图的分析,他肯定也是金质的,但他表现出来的是谦卑的,是敬畏的,绝对不是一帮小人就会影响到的,他的性情是稳定的,是成熟的,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柏拉图从反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失败本身也是一种成功。失败给我们教训了,让我们看到此路不通,你证明此路不通也是一条出路。
柏拉图在培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时候,最开头狄奥尼修斯二世还是受他一定的影响的,不过这个种子太浅了,一下又就被别人挤开了。据说,狄奥尼修斯二世对僭主这个称谓极端地厌恶,就是受柏拉图影响。有一次在祭祀当中,传令官按照祭祀的惯例,要诉求神,念祷告文,要求保佑狄奥尼修斯家族能够世世代代成为僭主。结果到没想到狄奥尼修斯听到以后就立刻大喊,不要诅咒我。僭主在他们看来本来是个好词,被教育受影响看来还是有成效的。就是我说的,种子播得太浅,听个“半吊子”就觉得我懂,其实没有懂,这个种子还没有发芽,还没在土壤里面扎根。
我经常会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扎根,你扎根了才能从内而外真正地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今天的诱惑太多了,知识本身也是一种诱惑,我们今天接触的知识五花八门。如果你每天看的知识都是蜻蜓点水,其实就永远没有扎根,你永远就是浮萍一样的。今天这个诱惑你,明天那个知识是好东西,第三天知识有好东西,完了,你跑了一圈,你在哪里?知识都是别人的,它不是你自己的。
哲学也是这样,观念也是这样。“相信种子,相信岁月”,这是南明教育集团的校训,“相信种子”是第一步,但重要的是“相信岁月”。一粒种子要成长,需要岁月,需要五年十年百年之功。做文化事业、做播种的事业是最难的,你还急不来。干教育,绝对不会说纠集一帮人,我们明天就成了,不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柏拉图的心态,其实这个心态跟孔子有点像。就是“无道则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你听我的我就劝你,你不听我的,我就到一边去。他说,“病人如果拒绝改变有害的生活方式,那么真正的医生就不应该再给这样的人提建议。同理如果政府开始按正确的方式运作,为了城邦的利益,他会听某方面的意见,我们就给他说,但如果政府完全偏离了正确的统治轨道,不愿意走正道,那只能为他祈祷。”有人概括说,柏拉图提出一种最佳政体,已经不是他所说的“哲人王”的政体,叫祈祷政体。所谓的祈祷政体就是这种政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能不能实现只能靠天意。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比如说美国华盛顿当时那种情况就是天意,你怎么去模仿,别的国家也学不来。谁学美国的民主,一学一个死。但可以学原则、学精髓,但你要把联邦制照搬肯定是行不通的。
我们说完狄奥尼修斯,再说狄昂,狄昂其实也是有统治的欲望的。狄奥尼修斯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头重脚轻根底浅,他没有扎根。狄昂是另外一个问题,哲学家面临巨大的诱惑和动机,就是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自己的国家。所以所有期望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他们的灵魂都有一个巨大的无法无天的欲望。就是说,即便你有哲学的根基了,但是你的欲望可能会随着你的哲学根基的加深越来越强烈,舍我其谁。你是好心,你看到这个国家生灵涂炭,你确实真的想出来振臂一呼。狄昂就是这样干的,太着急,狄昂坏就坏在太着急了。也是有无法无天的欲望,但这个欲望也会导致最大的威胁,就是丧失哲学本身。哲学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你有欲望的时候,你就会从属于政治暴力的诱惑,你就希望通过暴力去实现哲学的抱负,但是其实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哲学已经离你而去了,你已经不是哲学家,你是政治家了。哲学家一定只能从根本的、深层次的、观念层面、精神层面去塑造一个国家,塑造一个民族。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哲学或者哲人跟政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归纳了六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叫逍遥自在,远离政治。这个肯定是柏拉图不同意的,亚里士多德也不同意。政治是破败的,我们就跑到终南山里面做逍遥游,我就去不关心世间事物,但是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更何况当你掌握了哲学,你所有哲学的目的仅仅是让人舍去臭皮囊,舍弃这个世界吗?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通。哲学是事关人的学问,然后你告诉这个人,你要舍弃人本身,这个就有点矛盾了。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哲学家就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在书斋里面创造一座理论的大厦,不对这个时代严肃而重大根本的政治问题作回应,我觉得你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哲人。因为你的问题可能是假问题,你的哲学可能仅仅是看上去很美,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的。是假问题,你没有反映一个真正的问题,真正人性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们中国这种哲人的土壤是有的,大家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借口。我觉得最终还是对哲学的理解有偏差。《道德经》也没给你说,真的是要回到山里面去做逍遥游。
第二,是牛虻的使命,刺激政治。这个是苏格拉底干的事。苏格拉底也是个哲人,但苏格拉底说,我就是不能够从事政治,我就不会当“哲人王”。但是我有一个使命,我也不离开政治,我就是要让你讨厌我,但是我又不离开你,做一个牛虻,整天去刺激你,去批判你。到今天,我们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批判,你在任何政体下都要批判,这是真正的使命。批判的传统,我是认同的,但你怎么批判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做帝王师,支配政治,这个是有很多的传统的。我们知道后面最伟大的一个人叫做马基雅维利,他有马基雅维利的微笑。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献给当时美第奇家族的。他的献词看上去好像是非常的奴颜媚骨的样子,马基雅维利当然是想当“帝师”的。就是真正地作为一个影子式的统治者,垂帘听政,幕后听证,幕后去指挥这一切,这是一种乐趣。马基亚维尼那部喜剧《曼陀罗》,里面的李古潦就是这么一个人。
马基亚维尼
第四,货与帝王家,附庸政治。今天中国经常的好多人是这么做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实就是附庸于政治。他实际上是为政治做论证的,我觉得这是最可怜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哲学家掌握很多的逻辑,掌握的很多论证很有力量。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叫做论证?论证就是不挑战前提。我先承认你的政治前提是正确的,然后为你的前提写很多的文章,做注脚,说他多么有道理,这叫做论证。做论证其实叫政策学,不是学问。我跟王江雨老师聊,比如说郑永年,他也是很不错的学者,但还是在做论证,郑永年也是国师。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出新权威主义,所谓的论证就是,假定我们先承认有新权威主义,我们会找很多的政治学史上证据,论证得还挺漂亮,有学术包装,逻辑自成一统,这叫论证,不挑战前提。这已经不是哲学家了。我觉得哲人也不是纯粹的批判。批判是理性的批判,学理的批判。真正的哲人就是要对前提追问,追问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的前提在哪里,哲学家是要追问的。
郑永年
第五,被迫成王是最佳政治。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有了哲学知识,但他又不想做王,又被迫成为王。这个就被认为是最佳的政治。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这样最佳的政治?基本上挺难找的。这两者要结合在一起,柏拉图也说很难。
第六,塑造灵魂,回应政治,这个我会稍微赞同一点。当然我也不排斥,比如说牛虻的使命,还有被迫称王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哲人的使命是回应政治,他一定要回应政治,但他最终是为了塑造灵魂。你要改造政治,首先要改造灵魂,其实灵魂的塑造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哲人是教育家,哲学家是教育家。改造灵魂并不是洗脑,它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是一个对话的革命,是一个思想的革命。他内在会展开一个对话,然后让人们真正地明白什么是美好生活,为美好生活要真正做论证,当然同时为美好生活如何去实现也要做论证。美好生活不是乌托邦,不是画一个饼,一个乌托邦的力量也是来自于脚下的土地。所以说,向下扎根,向上仰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哲人。向下扎根越深,可能你会真正看得更清楚。
你不能光仰望天就把地下忘了,你如果只是扎根不抬头望天空,你就会陷于政治。还有一种哲人是绝望,就是陷于政治,对政治感到绝望。有些哲人确实看到很多东西,他一看到政治太强大没有希望,他就特别的绝望,也会抱怨等等,也有这一类的。包括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其实也是这种心态,就是以一种普遍的绝望的心态,不做学术上的努力和回应了,这个也不对。我说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深层次的回应。你既要进入这个时代,但你要超越这个时代。你与这个时代就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你与政治之间也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你的内心要保持思考的纯正和纯粹。但是你要深邃地洞察和理解政治的复杂性,要做到其实也蛮难的,我们就只能努力去做了。好吧,谢谢,交流一下。
谌老师,您好!今天的演讲还是一如既往,大气磅礴,哲理很深,跟上你的节奏还都是有点困难的。在柏拉图身上,用哲学为王导出了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命题就是,精神领袖跟世俗领袖如果一结合,一定是极权主义的,在现代的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反复论证。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被迫称王属于最大政治,您大概能推论出这些,但是很难找,我相信是不是还能找到一个,就是杰弗逊。杰弗逊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一任的国务卿,第三任的美国总统,他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硕果仅存的,不错的“哲学王”,我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
杰弗逊
谌老师回答:杰斐逊的思想,在美国的所有立国时期的政治家里面,他是最复杂的,他的思想应该偏向于非常小农主义,农业社会的思想,他实际上是非常强调周全,强调小国寡民,他反对工业化。当然杰弗逊在独立宣言时期,他写下了才华横溢的经典历史文献,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制定宪法的时候,杰斐逊是没有参加的。但那时他已经是声名显赫了,他在法国做公使,他没有参加。当总统其实他已经是第三任了,他第二次竞争失败,而且围绕他失败,汉密尔顿为此决斗。我更佩服汉密尔顿,在战争期间,他是华盛顿助手、勤务兵,是这么一个角色。汉密尔顿二十多岁就去当兵,三四十岁就是财政大臣,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就是他创立的,那个时代,他就知道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而且他一直是典型的联邦主义者,就是加强美国联邦的中央集权。如果没有汉密尔顿、麦迪逊这一脉络的努力,我觉得没有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强大。如果按照杰斐逊当时的那种治国思路可能还不行。
我的意思是,杰斐逊作为一个政治统治者,从思想史,从美国整个制度意义的层面,他当然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从制度推进来说,他相对来说,好像也不是太特殊。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钟摆,摆到右了偏左,摆到右了又偏左。美国的整个司法机制,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运作得如此良好完善,尤其在初期,那更得益于联邦党人的这帮很牛的人,包括最高法院。马歇尔是最高法院最伟大的法官,他真正使美国最高法院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本来是最弱的机构,但他把司法审查权抓到了,最高法院可以宣布总统的行为、国会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宣告无效。这个权利肯定是最大的。所以今天总统在最高法院面前都战战兢兢,人家那才叫真正的最高法院,是最牛的机构。想来我们都觉得只能望洋兴叹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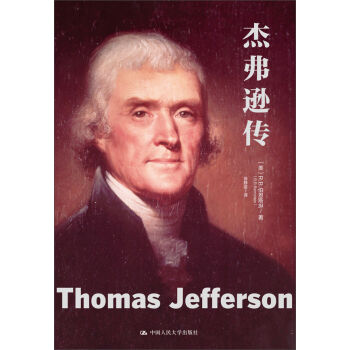
杰斐逊也很了不起,但我觉得至少统治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哲人王”。他作为总统的角色来说,基本上也算是过渡性的总统。从总统的本身,我觉得他没有太突出的东西,但他的突出在别的方面。
至于你刚才说的我同意,如果是精神领袖跟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确实是非常的危险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他其实不是精神领袖,是因为他成为政治领袖以后,被别人吹捧成精神领袖,更常见的是这么一种情况。在精神领域不存在领袖的,真的不存在,尤其是越伟大的哲学家,他越谦卑。他意识到在他之上是有神的,在他之上有更高的智慧的,他的智慧不过就是传达了,说出了一些神的奥秘而已。所以你看这些哲学家,没有谁敢说他真的是领袖,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好,谢谢。
- 第二十一讲:存在即超越,爱是通天路:《海的女儿》(下)59443:43
- 第二十二讲:道德的冤案与有限性的悲剧—— 《窦娥冤》解读(上)64645:53
- 第二十二讲:道德的冤案与有限性的悲剧—— 《窦娥冤》解读(下)49154:24
- 第二十三讲:侥幸真堪怜,糊涂因心魔——《红楼梦》中的葫芦案解读(上)74843:21
- 第二十三讲:侥幸真堪怜,糊涂因心魔——《红楼梦》中的葫芦案解读(下)69448:49
- 第二十四讲:哲人与政治的纠缠——关于柏拉图《第七封信》(上)72545:31
- 第二十四讲:哲人与政治的纠缠——关于柏拉图《第七封信》(下)53445:23
- 第二十五讲:解读阿里斯托芬喜剧《云》(上)63550:10
- 第二十五讲:解读阿里斯托芬喜剧《云》(下)61100:42
- 【你问果答 果老师Q&A】第六期:《法律与文学》25讲答疑20621:36













谢谢。